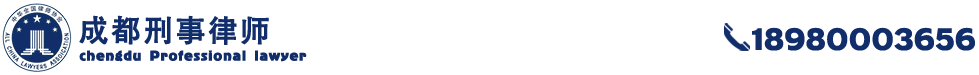电信诈骗“致死”如何定罪量刑?
新闻归顾: 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动静: 罗庄徐某电信诈骗案成功告破,主要犯罪嫌疑人郑某某(男,29岁,福建泉州人),黄某某(男,26岁,福建泉州人)等2人被抓获回案,其他犯罪嫌疑人正在追捕中。
另临沭宋某被骗案侦破工作取得重大入铺,已锁定2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及相关工作正在入行中。
法律点评: 两个大学生均因被骗郁结而死,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虽说“杀人偿命”,然而在本案当中要“杀人”的诈骗犯以命抵命,从理论上讲却是不可能的,甚至想对其苛以重责可能都存在着一定的难题。
从数额来望,徐某案和宋某案诈骗金额均在一万元以下,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详细应用法律若干题目的解释》(以下简称“《诈骗司法解释》”)第一条的划定,在一万元以下,仅属“数额较大”,根据刑法划定,只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如若通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其他诈骗犯罪事实,通过数额累加,无疑将会获得更大的处罚空间。
但从新闻表露的情况来望,犯罪嫌疑人“进行不久”,“业绩不佳”,诈骗数额巨大的可能性便又小了几分了。
从后果上望,被诈骗后郁结而死的危害结果令人愤慨,但这在刑法学理论上,仍属于“特殊体质”引发的小概率事件。
从理论上讲在行为人的行为只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诱因”的情况下,只有行为人能详细预见到被害人特殊体质,才能将死亡结果回责于行为人的行为。
而从糊口经验出发,一般人根本没有办法预料到诈骗9900元就会导致一个身体健康的年青人郁结身亡的危害后果,这样一个后果只能算作是意外,连过失都算不上。
固然理论是“理性”的,但实践中,也必需顾及人民群众的“感性”认知。
因此《诈骗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还划定了“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变态或者其他严峻后果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划定酌情从重办处”。
受骗后郁结而亡的后果,与被骗后自杀,精神变态具有对等性,故将其回进该解释的“其他严峻后果”应不存在障碍。
该解释实际上是从后果中央主义出发,以便在极端个案中,兼顾公平,可谓专心良苦。
然而“酌情从严的其他严峻后果”不是“加重情节”,更不能等同于“其他严峻情节”。
根据《诈骗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的划定,诈骗数额接近本解释第一条划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尺度,并具有前款划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属于诈骗团体首要分子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划定的“其他严峻情节”,“其他特别严峻情节”。
诈骗罪数额巨大的出发点是3万元,本案当中的金额连一万元都未达到,难以认定其接近“数额巨大”的尺度,那么即便其具有酌情从严的其他严峻后果,也不能破格认定其属于“其他严峻情节”。
如斯望来,法官是不是只能在“数额较大”的量刑幅度中对被告人予以从严从重处罚,即只能到三年为止了呢?笔者以为,也不绝然,另辟门路也未尝不可。
根据《诈骗司法解释》第五条划定,诈骗未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峻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
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划定的“其他严峻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一)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二)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三)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峻的。
实施前款划定行为,数目达到前款第(一),(二)项划定尺度十倍以上的,或者诈骗手段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峻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划定的“其他特别严峻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在本案当中,若公安机关通过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发送诈骗信息或者拨打电话的次数知足上述尺度的,公诉机关就有了可以指控其具有“其他严峻情节”的依据。
另外,通过精确把握个人信息,诈骗独生子女致其郁结而亡,造成极恶劣的社会影响,认定其为“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峻”好像也并不为过。
而即便法官在审理过程中认定了其未遂情节,但按照《刑法》第二十三条划定,对于未遂犯,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不是“应当”,法官仍可以判处至少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以儆效尤。
此外,值得留意的是,在徐案和宋案中,还存在着想象竞合的情形: 在两案中,诈骗犯分别冒充了教育局和公安局的工作职员入行诈骗的,根据《诈骗司法解释》第八条的划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职员入行诈骗,同时构成诈骗罪和冒名行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划定定罪处罚。
而《刑法》第二百七十九条关于冒名行骗罪是如斯划定的: “冒充国家机关工作职员冒名行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冒充人民警察冒名行骗的,依照前款的划定从重处罚”。
可以望到,冒名行骗罪,没有数额方面的要求,对于情节严峻也没有专门的司法解释予以限定,因此若认定其构成冒名行骗罪,法官就拥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完全可以将本案的情节认定为情节严峻,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实现司法公正与社会效果的同一。
结语 如何在极端个案当中在法律与道德,立法与实践间取得平衡,作出公正的指控,辩护与判决,十分考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专业功底。
然而没有人敢断言,这次暴露的个案是否仅仅只是个案,也许在我们视线无法到达之处,或前或后,都有其他无辜民众由于电信诈骗家破人亡,如斯,对个例的探讨将具备普遍的指导意义,当然这并非我们所乐见。
但愿通过对个案的不断深进探讨能重新唤起整个社会对电信诈骗这一社会毒瘤的关注,让悲剧不再重复上演。
(作者: 马成刑事律师团)